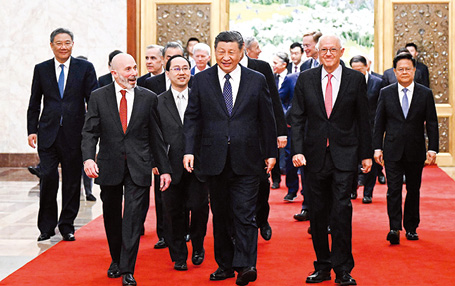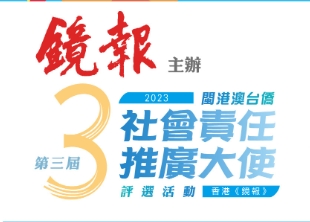大國地位動搖馬克龍壯志難酬
發布日期:2024-02-16 胡后法無論是在歐洲還是世界政治舞台,法國一直發揮着舉足輕重的作用。法國雖然接受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但在一些涉及本國及歐洲利益的重大問題上,並不完全與美國保持一致,而是積極探索踐行法國所宣導的「戰略自主」。法國是歐盟中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是歐盟中的唯一核大國。它和作為歐洲頭號經濟大國的德國一道,在歐洲地緣格局中發揮着「領頭羊」作用。然而,隨着國際格局的巨變,歐洲地緣政治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正當歐洲亟需法國發揮「力挽狂瀾」的作用之際,法國卻顯得力不從心,作為歐洲「政治引擎」的作用明顯今不如昔。面對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一大堆難題,法國政府並無應對良策。因窮於應付內政難題,曾經被視為充滿活力的馬克龍總統在一些關係歐洲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上再也無法發揮「一錘定音」的作用。法國的大國地位發生動搖,是當今世界格局演變的一個縮影,它無疑將對歐洲局勢乃至世界政治產生影響。
總理易人 困境依舊
1月9日,馬克龍總統任命34歲的加布里埃爾·阿塔爾為法國新總理,阿塔爾成為法國歷史上最年輕的總理,被稱為「政治神童」,此前他曾擔任國民教育和青年部長。一位政壇「小鮮肉」登上一個西方大國總理的寶座,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況且還不乏法蘭西式的浪漫,這位年輕總理還是同性戀者,其曾經的同性伴侶正是這次改組內閣後擔任外交部長的塞茹爾內,兩人於2017年正式宣布「結合」,但據說已於去年10月「分手」。
馬克龍之所以任命年輕的阿塔爾出任總理,據說主要出於兩大目的:一是為了防止其在剩餘的任期成為「跛腳總統」;二是想阻止極右勢力在法國政壇的日益壯大。然而,對阿塔爾實現這兩大目標,多數人表示懷疑。法國面臨的許多深層次問題,不是改組內閣就能解決的。馬克龍雖然於2022年再次當選總統,但民意支持率大不如前,社會不滿情緒上升,罷工、遊行、街頭鬧事等不斷擾亂社會生活,政府的行動能力受到制約,法蘭西社會進入了一個多事之秋,並已影響到作為世界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作用。
多年來,極右勢力在法國不斷發展壯大,成為法國傳統政黨的最大威脅。據最新民調顯示,代表右翼勢力的國民聯盟的支持率領先馬克龍所代表的復興黨10個百分點。今年6月9日,是五年一次的歐洲議會選舉投票日,這對馬克龍是一個「提心吊膽」的日子,因為各種民調顯示,極右翼的國民聯盟很可能名列前茅,成為法國最大的獲勝者。馬克龍所在的復興黨代表法國中間勢力,在議會中的席位並不佔據絕對多數,右翼勢力的崛起是馬克龍所代表的中間派政治勢力當前面臨的最大威脅,如果今年的歐洲議會選舉被右翼勢力超越,馬克龍政府的執政地位無疑將更加受到動搖。雖然年輕的阿塔爾將給政府注入活力,但要克服法國經濟、社會所面臨的深層次矛盾並非易事,其難度之大,任何政治家都會顯得回天乏術。所以,馬克龍寄予阿塔爾的期望很可能無法實現。法國右翼勢力的崛起,有着深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原因。要想完全挽回應對右翼勢力挑戰的頹勢,看來是幾無可能的夢想。對馬克龍而言,如能讓歐洲選舉不至於輸得太慘,就算是謝天謝地的了。
在全球化浪潮中,法國經濟面臨巨大挑戰,高福利、高成本打擊了法國經濟的對外競爭力。作為歐洲發達國家的通病,長期「養尊處優」的福利制度使法國社會缺乏創新動力,經濟結構陳舊,就業市場缺乏活力。除核能、航空、電子等製造業外,法國在國際上真正具有競爭力的優勢產業並不多,致使法國近年來經濟增長乏力,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國家債務居高不下,稅收負擔加重,制約了經濟社會發展。
雖然馬克龍在2022年再次當選總統時將改革作為施政重點,但改革必然涉及不同階層的利益,極易引發社會不滿,一有風吹草動,這種不滿便會導致社會動盪。近年來,法國先後出現了全球注目的「黃馬甲」運動,其動因正是政府徵收燃油稅在社會引起的強烈不滿。該運動持續時間之長、對經濟社會造成的損失之大,為法國歷史上所罕見。去年3月,馬克龍強行通過「養老金體系改革」,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遭到議會反對派和民眾的強烈反對,在法國主要城市引發抗議和騷亂。馬克龍出台養老金改革,其實是基於嚴峻的養老金困境。面對老齡化的加劇、財政赤字的惡化和社會的變遷,如果不進行改革,法國的養老金體系將難以為繼。目前,法國每年養老金支出已達國內生產總值的14%,遠高於經合組織成員國8%的平均水平。預計到明年,法國的養老金赤字規模將達100億歐元左右。本次改革還旨在解決目前制度中的不公平和不合理,消除某些行業的特殊待遇。任何改革都涉及社會階層的切身利益,而引發社會震盪正是政治家害怕改革的重要原因。
外交受挫 地位弱化
長期以來,法國的政治影響力在歐洲名列前茅,但由於缺乏經濟實力的支撐,法國的政治領導力必須得到德國的配合與支持。因此,法德一直是歐洲政治舞台上的最佳「搭檔」。冷戰後,歐洲在世界地緣格局中的地位明顯上升,歐盟的聲音一度極具份量,這主要歸功於法德兩大「政治引擎」在重大問題上的團結一致。然而,自默克爾辭去總理後,德國新政府基本失去了對歐洲政治的領導力。朔爾茨總理執政後,一直被大量內政難題所困擾,成為德國歷史上最沒有外交作為的政治家。在重大國際事務上,法德兩國已無法形成合力,有時甚至出現爭議和矛盾。法、德兩個大國作為歐盟軸心作用的喪失,妨礙了歐盟地緣作用的發揮,這反過來又制約了法國的國際影響力。
由於法德兩國在歐盟的核心作用日趨式微,法國外交上的自主意識也難以為繼。過去,法國雖然總體上與美國保持一致,但在涉及歐洲和法國切身利益的重大問題上,法國往往能堅持原則,敢於和美國唱反調。近來,法國口頭上雖沒放棄」戰略自主「的政治追求,仍然主張「歐洲走自己的路」,但在實際行動上並無表現。如在對俄關係上,法國一度傾向於與俄保持接觸,在俄烏戰爭問題上也曾有促和意向,但近來法國的態度已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沒有什麼差別。
法國新任外長塞茹爾內上任次日便起程赴烏克蘭,進行他的首次外訪,表達法國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馬克龍還宣布,法國將於近期與烏克蘭簽訂安全保障協定,這意味着法國對烏軍事援助的法律化,也意味着只要俄羅斯軍隊不撤出烏克蘭,法國等西方國家就將支持烏克蘭戰鬥到底。法國是繼英國後與烏克蘭簽訂安全保障協定的第二個西方國家,從而成為西方國家中援烏反俄最堅定的國家之一。
在可預見的將來,法國的獨立自主外交看來只能停留在「有雷聲,無雨點」的地步,而這正是法國大國地位衰落的必然結果。去年,法國在尼日爾的遭遇是對其大國地位的沉重打擊。有人甚至認為,法國被趕出尼日爾,象徵着法國將淪為二流國家。歷史上,法國是歐洲僅次於英國的殖民大國,幾乎整個非洲曾經都是法國的殖民地,二戰後,非洲國家雖然紛紛獨立,但法國並沒有放棄對非洲的控制。法國通過金融、貿易、政治等各種手段,從非洲獲取經濟利益和資源,半個多世紀以來,法國從非洲獲得巨大利益,助力法國重振大國地位。法國的高福利社會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從非洲國家收割利益和獲取資源的基礎之上的。
尼日爾也曾是法國的殖民地,法軍在尼日爾首都附近一直駐紮着大約1000人的部隊,在靠近馬里、布吉納法索的邊境地帶駐紮約400人。去年7月,尼發生政變,軍政府宣布解除與法國的所有軍事合作協定,要求法國撤離所有駐軍,並驅逐法國大使。馬克龍開始時態度強硬,但最後不得不接受現實。尼日爾新政權效仿了鄰國馬里、布吉納法索的做法,後者分別於2020年、2022年發生政變後,迫使法國撤離駐軍。
法國從尼日爾黯然撤離,意味着法國失去了在西非的重要戰略支點,昔日對西非的主導地位將不復存在。有專家甚至認為,如果失去在前殖民地的勢力範圍,法國就將很難匹配「世界大國」稱號,而只能成為蜷縮在歐洲的「小國」。
人口結構失衡 種族矛盾激化
近年來,法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外來移民人口不斷增多,種族矛盾日趨突出,「高貴的法蘭西文明」受到「稀釋」。近年來,因種族問題而導致的社會衝突和騷亂時有發生,不同種族間的兇殺案更是家常便飯,有的暴力襲擊事件造成數十人甚至一百多人死亡,一些惡性案件震驚世界,如一名車臣移民將一位法國教師斬首。
法國目前移民人口為680萬,佔總人口的10.2%,而非洲移民佔其中的47.5%。與此同時,法國白人的生育率日趨下降,外來移民成為法國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法國移民以穆斯林和非洲人為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法國經濟高速發展,從法國前殖民地的非洲國家引入大量移民,以補充本國勞動力的不足。隨着時代的變化,移民超出了法國的承受能力,對社會的負面效應日益突出。
外來移民不斷增多對法國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高生育率是穆斯林和黑人移民的共同特點,隨着時間的推移,法國人口中的外來移民比例不斷上升。由於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不同,這些移民來到法國後,很難與法國白人相融合,從而加劇了社會矛盾,擾亂了社會秩序,社會治理的難度越來越大。在巴黎一些以移民為主的社區,黑人甚至喊出了把法國白人趕出巴黎的口號。
此外,外國移民普遍教育水平低下,就業困難,很多人只能依賴社會福利,致使政府的財政不堪重負,福利制度面臨困境。由於移民造成的社會困境日趨突出,右翼政黨利用移民問題大做文章,挑起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反移民成為右翼政黨贏得選票的重要政治口號。在2022年的大選中,法國極右政黨「國民聯盟」候選人瑪麗娜·勒龐獲得41.46%選票,明顯縮小了馬克龍的差距,比上屆選舉高出近8個百分點,「國民聯盟」成為法國第二大黨。
可以預料,移民將是長期困擾法國的難題。歷史上,法國大肆推行對非洲的殖民,攫取大量財富,成為國家強盛的重要因素。今天,非洲移民大量湧入法國,給法國社會造成巨大困難,有人將這一現象視為是非洲國家對西方殖民歷史的一種回應和報復,雖然非洲國家不可能有這樣的官方意圖,但歷史的輪回往往是無情的,而這正是人類應當記取的嚴酷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