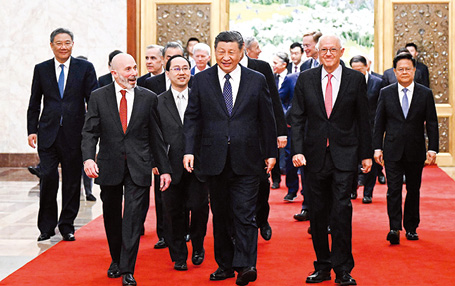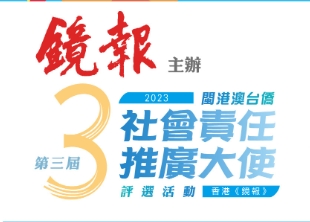法國南方畫鄉阿韋納橋
發布日期:2024-04-30 沈大力 法國若說法國楓丹白露森林西側遠近聞名的巴比松村為歐洲繪畫史上印象派的源泉,那布列塔尼菲尼斯特雷省的阿韋納橋鎮(Pont-Aven)則是十九世紀後半葉一些法國畫家另闢的美術淵藪。這批人被稱作「後印象派」,其實是逆印象派。因為他們是明顯逆反莫奈印象派的一端,最突出的當屬喬治.修拉(1859 -1891)首創的「點彩派」。
引起現代畫壇的迴響譽之為「魔咒」
阿韋納橋鎮位於阿韋納河邊,為一板石屋頂民房鱗次櫛比的聚落。阿韋納河水推動着多座鄉野磨坊運轉,維繫當地傳統的蕎麥或玉米烘餅食品業。鎮上有小教堂和鐘樓,當地居民不時舉行宗教遊行,顯示其不忘耶穌受難,隊伍間晃動着布列塔尼婦女們習慣戴的白色高端軟帽。阿韋納橋鎮自然風光綺麗,露草芊芊,田野綠綠茸茸,曲徑通幽,婉延伸至山坡,讓駐足行人遠望,遐思冥想,另饒生趣。
十九世紀末,一百多名畫家對這兒產生濃厚興趣,徜徉於藝術情感的漣漪中,形成了一個頗具特色的藝苑。最早到此地的是畫家兼作家埃米爾.貝納爾。他原籍里爾,1884年在高爾蒙畫坊見習,結識了圖魯茲.羅特萊克,繼而跟梵高、高庚、塞尚和奧迪龍.勒東數相往來,並同高庚一道,提出美術「綜合論」,宣導「隔色畫法」,於1888年在阿韋納橋鎮發起象徵派繪畫運動。
高庚於1886年7月第一次抵達阿韋納橋鎮,被當地離奇的景致所吸引。他寫信給友人弗奈克爾說:「我在這裡找到了原始的野性氣息。當我腳踏木鞋踩上花崗岩地面時,仿佛聽見深沉而又強烈的音響。這正合我的繪畫意象。」當年十月,他回到巴黎,後到法屬馬提尼克獵奇,途中染病,又身無分文,於1888年二月再次回轉到阿韋納橋鎮。一個夏日裡,他邂逅年方20歲的埃米爾.貝納爾。二人一見如故,都表現出對一度時髦的印象主義感到厭倦。高庚欣賞日本「浮世繪」版畫,正像貝納爾在《懸崖憩息》畫中所表達的,在畫布上塗抹用深線條勾勒的鮮艷色彩,如同彩繪玻璃窗邊緣映出的鉛華,或者琺琅瓷閃光的銅飾。
事實上,埃米爾.貝納爾提出的「隔色畫法」給高庚以深刻啟迪。在倆人述往思來的長談中,高庚得以完全克服他在畫《格洛雅奈克的節日》時流露的某種猶疑,擺脫了對色彩的直覺依賴,與印象派的現實主義徹底決裂。
《格洛雅奈克的節日》這幅作品,是高庚在1888年回到阿韋納橋鎮時畫的一幅靜物。其時,他下榻在格洛雅奈克旅店,此畫是他擬贈給女店主瑪麗-讓娜的禮物。畫作裡,他已經開始運用「隔色畫法」的新技巧來點彩。在深沉的線條形狀內,畫面色彩鮮明,圖形上既無陰影,亦無映景。無疑,他的創作影響了莫雷的《打麥農婦》和普伊果的《糙石巨柱腳下的農村少女》。二者都像他那樣體現出豪施色彩和層次節奏的創意。不過,在嘗試色彩並置效果上,高庚後來卻是跟修拉的裝飾隨意性相契合。
1888年,高庚在阿韋納橋鎮由貝納爾引見,同前來的畫家塞魯西耶相識。塞魯西耶來自巴黎朱利安畫坊,是新柏拉圖主義信奉者,跟高庚的理想主義一拍即合,畫起色調均勻的布列塔尼自然風景,用一小塊木板描繪當地秋色。
「你怎麼看這些樹木?」高庚發問,啟示塞魯西耶說,「它們呈綠色。那好,你就着綠色,用你畫板上最美的綠色。這兒的陰影部分用純深藍色,映出藍色閃光。至於紅顏色的樹葉,就採用朱砂紅吧。」
依照高庚的色調指點,塞魯西耶完成了畫稿。回到巴黎後,他將這幅作品拿給朱利安畫坊的同伴莫弗拉等人看,後者歎賞畫幅均勻的清純色調,一致稱讚這幅畫既無凸突,亦無深凹,會引起現代畫壇的迴響,譽之為「魔咒」。
1889年5月,巴黎國際博覽會開幕,高庚與其同伴趁此際遇,搞了一次畫展,專呈阿韋納橋鎮畫派的藝術特徵。由沃爾.比尼出面,眾人開設了一家咖啡館捧場。高庚乘勢揭示美術界學院派的虛偽和印象派的衰頹,以他為首的阿韋納橋鎮畫派提出:「回到原始開端,返歸人類共同源泉」。
高庚的獨特繪畫藝術主張給予一些敢想敢闖的年輕畫家創新啟示,其中有彼埃爾.波納爾、愛德華.維約爾、和阿里斯蒂德.馬約爾等一批畫壇才俊。他們給自己冠以「納比」的頭銜(希伯來語意為「預言家」),另衍生出一個繪畫派別。
高庚和荷蘭籍畫家梵高是經貝納爾舉薦結識的。二人有過一段不幸的交往。梵高於1888年2月到法國南方的阿爾勒城定居,幻想在那兒建立一個藝術家的「法郎吉」,特邀高庚到彼一敘。可是,二人秉性不合,一夕交談驟生激烈衝突。一怒之下,梵高割掉了自己一隻耳朵,鮮血淋淋,嚇壞了高庚。極度失望之下,高庚離開友人住所出走。1891年4月,高庚離開阿韋納橋鎮,經馬賽港乘船遠赴新喀里多尼亞的塔希提。他說:「我遠去尋求安寧,只想從事簡樸的藝術。為此,我需要重新在原始的大自然中浸浴。」 高庚窮途幽情,瑟縮在異域,獨自另立門戶,終了遇疾,銜恨而逝。
為歐洲畫壇另闢出一條蹊徑
高庚離去後,他在阿韋納橋鎮點燃的星星之火並沒有自茲熄滅。高庚無疑是阿韋納橋繪畫「法朗吉」的烏托邦主。他對歐洲二十世紀德蘭、畢卡索和莫迪格利亞尼等傑出畫家和雕塑家產生了相當的影響,特別是他的色彩觀,給馬蒂斯的野獸派打上了深深的印記。莫里斯.德尼對高庚的傳習銘之於心,繼續挺舉阿韋納橋畫派的旗幟,光揚「綜合主義」,力主回歸原始,在繪畫理論上主動發揮納比派藝術家們的特殊潛力;巴黎市中心香榭麗舍劇院的天頂畫就是由他繪製,其主要美學著作有《現代藝術與宗教藝術新理論》(1922年)。另一阿韋納橋派畫家莫雷(1856 - 1913)則在大型風景畫領域頭角崢嶸。此外,該派還有兩個畫家莫弗拉和麥耶.德.阿安也各有建樹,後者尤以其爽朗畫風博得同行讚許。在十九世紀末葉,阿韋納橋畫派與修拉派合流,拒絕莫奈印象派強調光線色彩瞬間效果的舊套路,而注重物象靜態和靈爽特質的點彩新技巧,為歐洲畫壇另闢出一條蹊徑。
若論阿韋納橋鎮的聲譽,可看1975年出品的法國影片《阿韋納橋鎮的烘餅》。該片描述阿韋納橋派畫家輕佻的處世態度,折射出他們對美術的體察和生活感受,可謂這一地域畫家的剪影或習俗透鏡。在十九世紀末為六角國展示了一個繪畫「法朗吉」的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