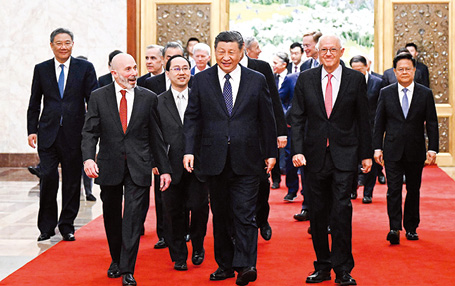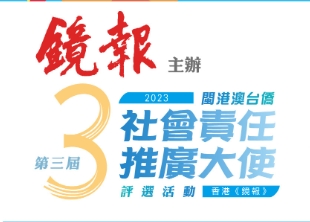讀書人王素
發布日期:2024-04-30 林青「我有很多工作都是隨機隨緣,其實,我只想做一個讀書人。」王素對記者說,不時推一下陷在眼窩裡的眼鏡。
王素,1953年10月生於湖北省武漢市。現為故宮博物院研究館員、故宮博物院學術委員會委員。
作為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獻的歷史學者,王素從20世紀80年代起,開始參與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並逐漸成為中國整理出土文獻門類最多的學者,依次整理了文書、墓志、簡牘、甲骨,並即將開展金文的整理項目。
2023年3月,春日明媚,記者在號稱亞洲第一小區的北京天通苑見到了王素。「從天通苑到故宮上班1小時零5分,這個時間對我來說再熟悉不過了」,與北京普通打工者一樣,王素早已習慣每天地鐵通勤,只是,整理出土文獻、填補歷史空缺,王素並不普通。
「素」的來歷
王素出生的那些年,內地流行給孩子取名「建國」、「建軍」、「衛國」、「衛東」。「素」這個名與那個年代的風格迥然不同,王素說,「素,是父親對我的寄托。孔子,無天子之名而行天子之事,號稱『素王』。父親取此名,希望我在治學方面,成為一個專精的學者,能夠為人師表。」
「父親有這樣的希望,與他不堪回首的過去有關。」他是一個文人,1944年,曾考取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研究生,這個位於重慶的學校,是蔣介石準備傳位給蔣經國,為其培養幕僚準備的。「彼時,父親思想左傾,憤恨國民黨的腐敗作風,終被開除。」之後,他考入震旦大學,又考取清華大學。然而,那時人們顛沛流離,父親也經歷了輟學、入伍、轉業,生活波折不斷。新中國成立後,他回到武漢安家,成為中學教師,卻經歷「文革」挫折。「父親一生志向遠大,但懷才不遇,所以對我的期望非常高」。
王素說,父親常引古人言:「有子能讀父書,乃人生一大幸事!」在父親的教育下,王素6歲開始背詩詞,9歲開始寫詩詞,13歲後涉足史林,系統閱讀「二十五史」,並曾抄寫兩遍《說文解字》。中小學期間,正值內地「文革」時期,王素一直在家苦讀,「我知道父親讓我讀書,是為我好,最逆反的年紀,我一點不逆反,對他的話言聽計從」。
那時,王素自己定任務,一天平均背一首詩。長詩如《離騷》,幾天背會,短詩如五絕、七絕,一天要背多首,這樣一直堅持,24歲考大學前,王素已背得詩詞近4000首、古文近400篇,並通讀了《十三經》、「二十五史」、「全通鑒」、《百子全書》及《困學紀聞》、《日知錄》、《十駕齋養新錄》、《陔餘叢考》、《廿二史札記》等重要文史典籍。
1977年,內地恢復高考,王素考取武漢大學歷史系本科,次年考取「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專業的碩士研究生,入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唐長孺門下。
王素一直以「唐師」尊稱唐長孺,在入唐師門牆之前,已向其書信問學了兩年。第一次給唐師寫信,是1976年夏秋之交,那時「文革」還未結束,王素下農村後回城,在武昌煤建公司當送煤工人,自感前途渺茫,給唐師寫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談自學古典文史的經過,並附上「證明」自己國學功底的五首七律。大約一個多月後,唐師回信道,「你的詩詞寫得很好,證明你確實學有素養」等等,最後在信中說,希望春節約王素見面。
「我的喜悅和激動自然不可言喻」,王素回憶,1977年春節的一個晚上,他見到了唐師,「當時,唐師66歲,童顏鶴發,慈眉善目,很是客氣,使我減少了一些畏懼感。」
王素雖然年輕,文史基本功卻非常紮實,成為唐長孺最器重的學生之一。當時,唐長孺兼任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主任,正在主持《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工作。他1978年招了8個研究生,「他認為,只有我最能坐『冷板凳』,適合文書整理工作」。於是,1981年,王素畢業後,分配到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協助唐長孺從事文書整理工作。
從吐魯番文書起家
「古文獻研究室曾是內地官方成立的唯一的專業整理和研究出土文獻的機構。出土文獻有五大門類:甲骨、金文、簡牘、石刻、文書。我是從整理吐魯番出土文書起家的,做了一輩子出土文獻整理工作。」
1959年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新疆吐魯番的阿斯塔那和哈拉和卓古墓群進行了十餘次科學發掘,掘得漢文文書近萬片。1975年,成立了由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和武漢大學歷史系三個單位組成吐魯番出土文書整理小組。
「從事出土文獻整理工作,能夠見到並觸摸原件,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我負責校訂文書釋文和編輯文書圖文對照本,工作要求盡量認真仔細。」從1981年到1996年,王素每天到沙灘紅樓上班,「一天工作10多個小時,很有幹勁」。
由於這批文書的出土地在晉唐時期屬於邊疆,不僅和中原文字存有一定差異,還摻雜了大量民間俗別字,需要逐一「隸定」成今天通行的文字,給整理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戰。
那些年,三個單位的同事一起,拼得文書近1800件,均按原式抄寫影印,有關文書本身的情況,如墨色、殘缺、衍脫等,也要一一標註,最終整理出版了《吐魯番出土文書》釋文本10冊,圖文對照本4卷,「這是一件太了不起的工作」,王素感嘆。同時誕生了一門新的學科—— 吐魯番學。
自參與文書整理工作起,學界對王素的工作就給予了充分肯定,不少國家級出土文獻整理項目都邀請他參加或主持。
1992年,古文獻研究室領導找王素,委托他主編《新中國出土墓志》。「墓志是石刻文獻,是非常特殊的存在。古代墓葬例有碑志,碑立在墓葬外,志存放在墓葬內。墓碑在外風吹日曬,損毀得很厲害;墓志在內密封,則通常保存良好。這些墓志有不少出自著名藝術家、書法家、文學家、史學家之手,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文獻價值。」
《新中國出土墓志》工作開始不久,1996年,長沙走馬樓出土了大批三國吳簡,有10萬餘枚。彼時,「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田餘慶負責吳簡整理工作,點名讓我參加,我不敢怠慢。」而由於這批吳簡字跡很多殘缺漫漶,王素的眼鏡度數在此期間迅速向上攀升。
即便如此,王素說,「我非常熱愛我的工作,也只有在整理出土文獻的時候,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展現我文史兼通的功底。」就這樣,王素一口氣參與多個國家級重點項目,工作強度和壓力「都挺難想象」。
與此同時,王素還利用業餘時間,做自己感興趣的歷史研究,其中,用力最勤的是撰寫了兩部《高昌史稿》,王素也因此被學界稱為「高昌王」。
「《高昌史稿(統治編)》和《高昌史稿(交通編)》,這兩部書,我逐字推敲,從1989年立項起,寫了將近10年。如果從1982年醞釀算起,則用了將近20年。」王素說。
歷史上的高昌,即今日的新疆吐魯番地區。從西漢開始,就是中西交通的樞紐。各種商品在這裡集散,各種民族在這裡過留,各種語言在這裡行用,各種文化在這裡交流。然而,如此著名的古代國際重鎮,當時的發展情況,除了正史中的《高昌傳》略有記載外,其餘都不得其詳。
由於參加吐魯番文書整理,王素接觸到大量出土文獻,他結合傳世文獻記載,參閱國內外研究成果,對先秦姑師與車師前國至唐太宗滅高昌(公元640年)這千餘年吐魯番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梳理和研究。
王素說,「我對高昌史特別感興趣。若沒有出土文獻,僅據傳世文獻,寫不出高昌史;只能專攻一隅,不能博綜文史,也寫不出高昌史。這兩部《高昌史稿》的完成與出版,最大價值是填補了中國地方斷代史的空白。」
整理甲骨「從零開始」
2006年,王素調入故宮博物院研究室。2013年,故宮成立古文獻研究所,王素任所長。那年,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單霽翔壓力巨大,因外界指稱,故宮有22000多片甲骨,下落不明,讓故宮給學術界一個交代。這樣,王素臨危受命,不得不又承擔起故宮甲骨的整理工作。
據已故著名甲骨學家胡厚宣曾經的統計,故宮博物院藏有殷墟甲骨22463片。王素介紹,據最新調查統計,包括民間收藏在內,世界現存殷墟甲骨共約16萬片,故宮博物院藏殷墟甲骨約佔總數的13%強,收藏量居世界第三。
這些甲骨1949年就存放故宮庫房,但由於種種原因,只有4700多件在文物賬上有記錄,其他都作為「資料」束之高閣無人問津。原因與故宮古文字人才斷檔有關。譬如故宮自己的金石專家馬衡、甲骨專家唐蘭、璽印專家羅福頤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都已去世,此後幾十年缺乏古文字人才。
「接到這項整理工作時,故宮沒有任何積累,一切都是從零開始。最為緊迫的是人才培養。幸而故宮2012年成立了博士後科研工作站。我依托工作站,首先培養人才。」據王素介紹,目前,故宮甲骨項目的編目、攝影、拓片、摹文、釋文五個子課題組人員齊備,有故宮的資深專家,有外聘的一流技師,還有就是王素自己培養的博士後。
王素認為,整理出版故宮甲骨,本身具有重要學術意義。因為故宮甲骨絕大部分沒有公佈,屬於「甲骨文獻最後的寶藏」,一直受到學界關注,將其整理出版,對國內外甲骨文與殷商史研究一定能起到極大推動作用。
王素說,「目前,甲骨文與殷商史研究,是學界極為看重的工作。因為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但中國能夠編年的歷史從西周共和元年(前841年)算起,只有不到3000年,此前的夏和商一直被稱為傳說時代。甲骨文的發現和殷商史的夯實,將中國信史的時代向前推進了將近1000年。我們將故宮甲骨整理出版,為國內外甲骨文與殷商史研究提供新的材料,自然是一件具有重要意義的工作。」
不久前公布的《2021—2035年國家古籍工作規劃重點出版項目(第一批)》中,故宮有甲骨文,金文、陶文、敦煌吐魯番文獻四個項目。記者注意到,這四個項目,都由王素負責。王素說,「甲骨準備整理出版60卷冊,目前按藏家整理,只出版了《馬衡卷》和《謝伯殳卷》各3冊,已覺任重道遠。加上金文、陶文、敦煌吐魯番文獻,後面還有大量的工作。要想完成這些工作,需要進行學術傳承梯隊建設。」
王素說,自己這些年,有感於故宮古文字人才曾經斷檔,有意識地做過很多文化傳承和接續故宮文脈的工作。建設學術傳承梯隊屬於這些工作的一部分。此外,自己還給博士和博士後講解格律詩詞,希望文化基因能夠融入年輕人的血液裡,使文化能夠真正世代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