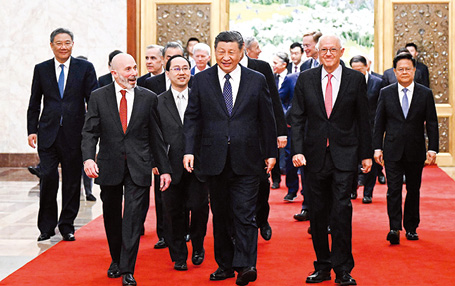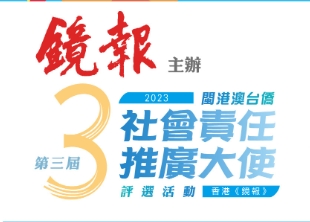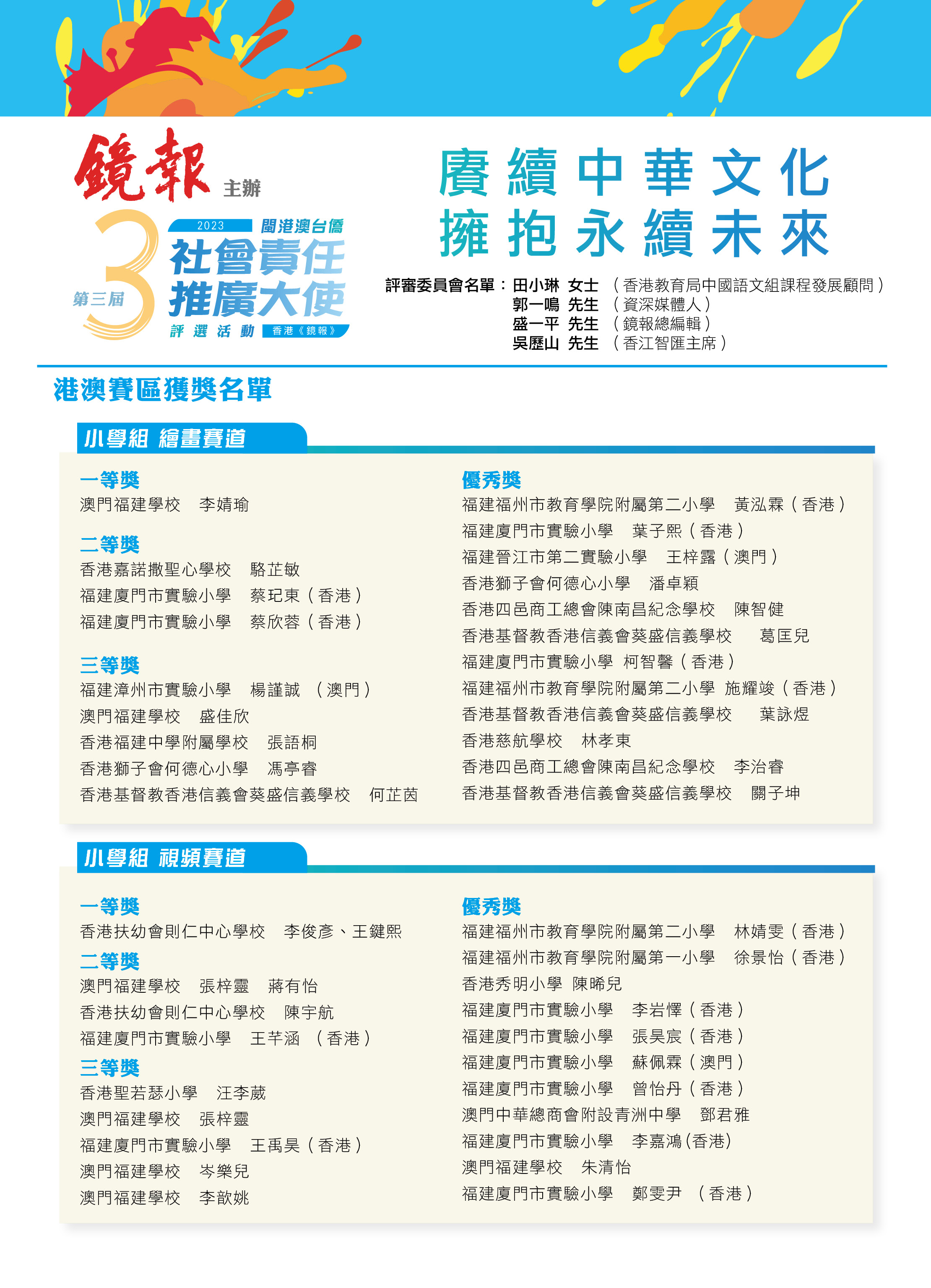韓國「醫罷」對香港有何啟示
發布日期:2024-06-04 文軒一名年僅2歲9個月的女童溺水後急需轉院做手術,卻被11家醫院以「人手不足」等理由拒收,最終在輾轉途中不幸身亡。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你所處的國度,你是否會對這個國家的醫療體制感到絕望呢?然而,這樣令人痛心的場景,正在韓國頻繁上演。
韓國政府於今年4月10日迎來國會選舉。2月6日,韓國尹錫悅政府選擇在選舉前發布長期遭受爭議的醫科大學擴招方案,遭到醫療界強烈反對。近萬名實習和住院醫生遞交辭呈、罷診離崗,造成診療混亂。據韓聯社4月的報道,首爾7家政府指定的大型急救醫療中心中,已有6家因人手不足減少或暫停了部分手術和治療,在崗醫生不堪重負。從全國範圍來看,44家急救醫療中心中超過9家無法正常提供急救服務。韓國醫療系統危機級別已提升至最高級「嚴重」。
觸碰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
此次韓醫罷工事件的成因是複雜的,但究其根本,還是觸碰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目前韓國人口約5169萬,卻只有不到13萬名醫生,平均每1,000人中僅有2.6名醫生,遠低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平均數3.7名。再加上韓國政府預計到2035年時,65歲以上的人口將比現在增加70%,屆時將面臨1.5萬名醫生缺口,故宣布從2025年起每年多招收2,000名醫學院新生。然而,自2006年以來,醫學院每屆的招生定額一直是3,058名,此次擴招相當於激增了65%,迅速引起當地醫療界的強烈反彈。
2月26日,韓國100家醫院已有10034名實習和住院醫師遞交辭職申請,其中9006人離任。儘管尹錫悅政府態度強硬,祭出吊銷執照、坐牢、服兵役三招作為威脅,但罷工情況並未好轉。3月25日,許多醫學院教授也決定集體辭職,雙方依舊拉鋸。直至尹錫悅所在的國民力量黨在國會選舉中慘敗,包括國務總理在內的多名高官請辭,尹錫悅對醫生罷工的態度才漸趨緩和,這場醫政博弈有了逐漸轉入尾聲的跡象。
韓醫罷工抵制擴招的堅決態度與香港頗為相似。香港同樣面臨公營醫療人手不足的問題,根據立法會數據,在2021年,香港平均每1,000人中只有2.1名醫生,甚至還不如韓國。但由香港醫生團體掌控的醫務委員會,對於放寬招收海外醫生的堅決抵制態度與韓國如出一轍。這就值得引起我們正視,正如早前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談到韓醫罷工之時,就特別強調香港醫護界要「引以為鑒」。
醫生無論在韓國還是香港,都是十分光鮮的職業。被稱為「白衣貴族」的韓國醫生更是世界上收入最高的醫生群體之一,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統計中名列前茅,且明顯高於韓國平均薪酬水平。據OECD《2023年衞生統計》報告,韓國受薪醫生2020年的平均年收入達19.3萬美元(約150.5萬港元),開設診所的醫生平均年收入為29.9萬美元(約233.2萬港元)。相比之下,德國醫生的年度平均收入為18.8萬美元,法國則為9.9萬美元,OECD成員的平均水平則為10.8萬美元。因此不難想象,韓國人口在持續下降,如果擴招醫生,現有的高收入肯定會因為分利者增加而減少。
與此同時,韓國醫學教育走的是精英路線,出類拔萃的學生才能考入醫學院。進入醫學院後,除了長達六年的課程和實習,還須繳納高達2.5億韓元(約143萬港元)的學費,相當於韓國月薪中位數的100倍。醫學生在畢業前,還需要參加嚴苛的醫師資格考試,然後再進行為期一年的實習和4年的住院醫生培訓,才能成為一名專科醫生。
在香港,醫科生同樣是「天之驕子」。每年DSE考試的滿分狀元報讀醫科已成慣例,醫科生要成為專科醫生所耗費的時間與韓國相當,成為正式醫生後的收入也較韓醫不遑多讓。激烈的競爭,高昂的學費,以及超過10年的培養期,花了那麼大的勁才成為「人上人」,一旦放寬醫生就業門檻或增加醫生數量,之前努力付出的含金量豈不是大打折扣?正因如此,兩地的保護主義才如此根深蒂固,哪怕韓國見習醫生和住院醫生每周工作時數平均高達93小時,每月收入僅為350萬至400萬韓元(約2萬及2.4萬港元),仍毫不猶豫地充當了罷工主力。
保護主義阻礙醫療改革
值得留意的是,強烈的保護主義直接損害的是病人的利益,兩地都曾多次發起醫療改革,希望改變醫權獨大的現象,但最終成果均不如人意。據韓媒報道,韓國近70年來共有9次大型醫生團體發起抗議行動,最後都是以醫生訴求獲勝收場,無一例外。最近一次醫生罷工是在2020年7月,時任總統文在寅當時提出從2022年起每年增加400個醫學院招生名額,引發住院醫生集體罷工,大韓醫師協會隨後發起更大規模的無限期總罷工。由於當時疫情嚴重,當局最終妥協,同意暫緩推動相關政策。
在香港,阻礙醫生擴招的最大障礙是由醫生團體控制的醫務委員會(醫委會)。目前外地醫生如要來港執業,必須先在香港通過醫委會舉辦的、由三部分組成的執業資格試,包括專業知識、醫學英語技能水平和臨床考試,當中許多內容艱澀生僻,日常工作中幾乎完全不會涉及,被外界批評為「故意刁難」「抬高門檻」。就算三重考試全部合格後,還要擔任一年駐院實習醫生,接受在職培訓、評核及臨床指導,才能正式註冊成為香港醫生。特區政府於2016年提出醫委會改革,增加業外委員,以減少醫生團體對醫委會的掌控,竟被時任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一人「拉布」而拖垮了整條草案。
同樣的成長之路,同樣的保護主義,香港是否會重蹈韓國的覆轍,應該引起本港各界的重視。其實,韓國醫療改革的阻力之所以如此之大,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醫療體系高度私有化。韓國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搞全民醫保,但當時並非為了國民,而是出於與朝鮮的意識形態之爭,不願輸給朝鮮的全民免費醫療。但當時的韓國國力並不足以負擔這筆巨大開支,便逐步讓私有資本介入,以減輕政府壓力。截至2022年,韓國對醫保的財政支持比例已降至11.6%,遠低於其法律規定的20%的下限,私立醫院在醫療領域中的佔比則飆升到了95%,逐步為財閥所掌控,當代韓國「五強」醫院全部都是私立醫院。
更為可悲的是,韓國政府作為財閥利益的代言人,明知無法撼動高度私有化的醫療體系,卻屢屢利用國民對「醫權獨大」的不滿,提出醫療改革為自己增加支持度。而醫生團體既有財閥的背後支持,也早已清楚政府的底牌,自然有了誓死不屈的底氣。所以,尹錫悅的這次醫療改革,是一場從一開始就已知道結果的鬧劇,博弈雙方都七情上面地演着各自的戲碼,唯獨民眾的生命健康成為了無辜的犧牲品。
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
香港醫療的公私營比例雖未到韓國如此極端的地步,但亦處於嚴重失衡的狀態。根據衛生署的統計數據,以全港專科醫生比例為例,約有45%專科醫生於公立醫院服務,照顧全港近九成住院病人;其餘約 55%私人執業專科醫生,僅照顧全港一成私家醫院病人。嚴格來說,香港並不是缺醫生,而是公立醫院缺醫生,而阻礙公立醫院增加人手的最大障礙仍然是醫委會。儘管2018年醫委會改革取得一定進展,新增了四名業外委員,但醫委會32席中,仍有24席是醫生;8席業外委員中,4人由政府委任,1人是消費者委員會委任,餘下3名由病人組織選出,支持醫生利益的仍佔絕大多數,這也是改革六年來成效不彰的主因之一。因此,醫委會未來不僅要繼續改革,而且要不遺餘力地改革。
另一方面,公私營醫療比例亟需調整。目前近九成醫生未做到退休便已離開公立系統,且約八成未及顧問級別,流失率最高的年齡層為40歲以下。公立醫院工作重、壓力大、薪資也不具優勢,大部分醫生最終流向私人市場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故增加人手以緩解壓力、調整薪資以平衡落差、加大表彰力度以提升其使命感,均是可行之舉。
為官者仁政,為醫者仁心。醫生這一職業之所以崇高,從來不在於其社會地位,更不在於其收入多少,而是在於其奮不顧身救死扶傷的無私精神。韓國醫罷事件讓我們再次驚醒,決不能讓關乎百姓生命健康的行業被一小部分人所掌控。我們不僅要大刀闊斧地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同時還要重視醫生的培養制度,把立德樹人放在首要位置,培養出醫德雙馨的高素質醫學人才。